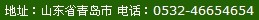|
作者郭克俭生活照 请输入标题bcdef 郭克俭(~),男,博士,中央音乐学院出站博士后,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传统音乐表演体系研究》首席专家。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新世纪优秀人才第二层次。 先后在《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等国家核心杂志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舞台艺术》全文转载;撰著《声歌求道》、教材《戏曲鉴赏》等五部;学术科研成果《新中国声乐学术热点问题的追溯与反思》获教育部第六届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政府奖)。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新中国声乐史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豫剧演唱艺术》等省部级以上课题十余项。 请输入标题abcdefg “婺剧”是对长期表演于金衢及周边地区戏曲舞台之高腔、昆腔、乱弹、徽调、滩簧和时调等六种声腔的统称,若从高腔算起,大约有年的传承历史。作为一个“多声腔剧种”概念的存在,则时间并不算长,学界存有年[1]和年[2]两说。近来有学者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考证,在核查相关的文字资料调查和采访了相关健在的知情当事人所获得的新材料的基础上,经过缜密的分析、综合与甄别,得出“婺剧这一名称最初出现于年谭伟等人组织的‘金中婺剧研究社’,次年因为某种原因官方的金华专署文工团也开始使用这一名称,直至华东戏曲改革干部工作会议以及后来的周春聚班改名婺剧团,即成为正式称谓。”[3] 六十年来,“婺剧”作为统合“高腔、昆腔、乱弹、徽调、滩簧和时调”六种声腔的“剧种”概念指代,不仅为从业群体所认可和使用,并且也被该地区的观众群体所普遍接受,二百多个专业和业余婺剧团常年活跃于农村草台,“婺州民众正是在跨文化审美比照中通过婺剧这种传统文化获得了自我体验和身份认同。”[4]但与此相反,婺剧理论工作者关于“婺剧”命名科学性、合理性等问题的质疑依然时有所见,本文拟从戏曲腔调衍变的轨迹出发,以剧种概念的视角探讨“婺剧”命名的有效性,就教于方家。 一 中国传统戏剧(曲)在八百多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约略经历了风格各异的南北曲、句式长短相间的昆弋腔、齐言对偶的乱弹诸调、自由多变的地方小戏四个时期。从戏剧音乐风格艺术特征上说,除南北曲裂变融化于后世的戏剧“调”、“腔”之中外,后三个时期的各类别“调”、“腔”则是处在争竞继替的交互并行之中的。 中国戏曲作为一个融时间、空间、文本、符号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表演艺术样式,不同戏曲品类之间的差异,体现在音乐、美术、文学、造型等方方面面,但主要还是表现为演唱音调、腔辞的不同,特别是对于向无固定文字脚本、长擅于“依心、依情”歌唱的民间“提纲戏”、“路头戏”等地方戏剧而言,则表现的更为明显。 入明以来,赏听戏剧成为时人生活中最高级别的艺术享受,特别是自嘉靖年间开始,城市官宦蓄养家伎之风盛行、乡村风俗典祭必邀班于庙台演戏,演剧市场需求的增益,促进了戏曲艺术的传播与交流。到了清朝雍正执政,为了整饬官风,下搬诏书严禁士绅官宦蓄养伶人;乾隆即位,维持风化,重申禁令。“雍乾间士大夫相戒演剧,且禁蓄声伎”[5],家乐戏班、官署戏班解散,大量演员和乐人为谋生计,流落民间搭班演出,高水准艺人的加入,表演范围的沿扩,戏曲音调在大范围传播的过程中,为适应各地乡土戏迷欣赏习惯的需求,势必要与各地不同方言语音给予结合,语音声调时值的改变,便演化派生出各自具有地域品性特征的“腔”、“调”,即王骥德所说“世之腔调,每三十年一变,由元迄今,不知经几变更矣。”但总的说来则是“声各小变,腔调略同”[6]。将这些经过本土化衍变的“腔”、“调”冠以地方域名、特征乐器名或艺术情感特征等,便成为区别中国传统戏曲品类名称的有效标示。 于是,就有了被后人誉为“四大声腔”的明代的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弋阳腔等“腔”,及其后的义乌腔、青阳腔、徽州腔、乐平腔等诸腔的出现;有了京腔、秦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腔等称之为乱弹的“花部”诸“腔”,以形成与“雅部”昆腔争竞之势,及众所周知的“花雅之争”。以及徽池雅调、高调、平调、浙江调、浦江调、祥符调、豫东调、豫西调、沙河调、时调等“调”,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戏曲中所称谓的“腔”或“调”的概念,则“既是一种戏曲音乐(包括唱调、伴奏、音乐形式)自身的概念,又是一种戏曲品种(涵盖剧本、舞台艺术)总体的概念。”[7]在中国传统戏曲文献和演剧实践中是没有“声腔”、“剧种”的概念,戏曲种类之间的分辨是以班社艺人所演唱的“腔”、“调”为依据并名之的。 演剧市场激烈的竞争,激发了艺人的艺术创造力,戏曲的“腔”、“调”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许多“腔”、“调”内部又派生出数目不等的“腔”、“调”子项,给戏曲品种的分辨带来了诸多的不便,至清末,戏曲叫法一度出现相当混杂的状况。如皮簧腔中就有徽调、汉调、京调;同为河南梆子腔则有祥符调、豫东调、沙河调、高调、豫西调之别,祥符调又称中路调;豫东调又称归德调[8]、下路调、东路调;沙河调又称南路调、安徽称“淮北梆子”;高调又称北路调;豫西调又称西府调、西路调。同一戏曲品种出现千差万别的称谓亦不鲜见,如为国人家喻户晓的“京剧”,之前先后有过乱弹、簧调、京簧、京二簧、二簧(二黄)、黄腔、皮簧(皮黄)、京班、京调、京腔大戏、京戏、平戏、旧剧、国剧、平剧等十五种称谓;形成于20世纪初并为国人所熟知的“评剧”、“越剧”同样是称谓颇多,前者又名平腔梆子戏、唐山落子、蹦蹦戏;后者曾名曰的笃班、小歌班、绍兴文戏、女子文戏等。 二 晚清以后,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称谓混乱所带来的诸多不便,仿借西洋舞台艺术“Drama”的形式,开始以“戏”、“剧”为中国戏曲命名,并在一些较早接受西式文化艺术熏陶的知识分子的见诸报刊的文字中出现,“由清末到年前,总的变化趋势,是向以‘戏’、‘剧’定名的剧种概念上统一。”[9]率先以“剧”命名的聚合海盐、弋阳、昆山、梆子等腔调的广东“粤剧”,时间大约是清光绪年间;年前后,旧称“楚调”、“汉调”在汉口改称“汉剧”;年,旧称流行于黄陂、孝感一带的“黄孝花鼓”、“西路花鼓”改称“楚剧”;年,俗称“小歌班”的“绍兴文戏”改称“越剧”;年夏,演唱“河南梆子”的兰州中州剧院更名为新光豫剧团,第一次将“豫剧”的概念由“河南省戏剧总称”限定为“河南梆子”。但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在戏曲的行内行外,抑或是文化知识阶层,此时段并没有形成“剧种”概念的自觉,因此,这种命名在起初并未见得能够得到戏剧圈内外的情感认可。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传统戏剧舞台艺术改革实践及学术研究的现实需要,借鉴国外戏剧的通例,几经权衡、推敲之后,以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戏曲改进局”的设立为标志,“戏曲”作为统合宋元以降的中国传统戏剧的概念沿用至今,有学者屡次对这一既非历史传统,亦非学术定义,产生了多方面副作用的行政行为的概念表示不解和反对。[10]但历史地看,用“戏曲”命名将宋元以来“以歌舞演故事”的综合性舞台艺术从中国传统戏剧中剥离,以区别于从西方传入的“说”的舞台戏剧艺术——“话剧”,亦不无合理与科学的可取之处,至少对凸显宋元以降中国传统戏剧的综合性歌舞艺术特征是不有帮助的;至于是否纯属行政所为,可能也并非如此简单,也许尚存有待考证之处,当然,题外之言,此不赘述。 自年代始,中国戏曲理论界开始出现并使用了“声腔”的概念,以此涵括、纳容了上位概念的“腔”、“调”的称谓,而一种“腔”、“调”在传播过程中,所繁衍、变容出来各不相同的支派,称为“声腔系统”,简称“腔系”。如高腔,在其由明代的弋阳腔与青阳腔结合生成之后,流传四方并相继被各地本土化,便形成高腔系统。形成声腔系统约略需要满足“继承关系、历史原因、语言因素、地方音调和社会条件”[11]五个基本条件,以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例,以“高腔”申报入选的有西安高腔、松阳高腔、岳西高腔、辰河高腔、常德高腔及新昌调腔(高腔)六种,而入选的川剧、湘剧、各地傩戏和目连戏等均以高腔为舞台表演的主要声腔,想必各地没有参见申报或申报没有入选的“高腔”还有许多,这就是高腔在全国各地流传、衍变,所派生出的结构庞大的“高腔系统”的当下存见。 由此,“声腔”便自然而然地替代了“腔”、“调”的概念,部分地承担起区分“戏曲品种”的功能。但对于纳容多种声腔于身的一些戏曲类型而言,单独的某一“声腔”概念,就因母项无法涵括所有子项而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剧种”的概念便呼之欲出,从此,各地方戏曲(包括单声腔剧种)便不再以声腔的称呼命名,取而代之的则是以“戏”或“剧”分别与流行地域、主奏乐器、所属民族、艺术表现特征等组合命名,而一些宗教祭祀仪式戏曲则是以表演题材为区分标准的,如傩戏、目连戏、醒感戏等,剧种概念的自觉就此养成,开启了中国戏曲(剧)艺术实践与研究的新篇章。以年统计的个剧种为例,除少数如秦腔等剧种外,基本符合这种命名规范,形成剧种命名的通则。 三 达成声腔、剧种概念的共识,“声腔”和“剧种”的同异便很清楚,二者除具有相同的能指外,更有明确的相异所示。也就是说,一种声腔可能随所传播地域的不断扩大,同时会被诸多剧种所纳采化用;而一个剧种出于演剧市场竞争与自身发展的需要,可能同时吸纳若干种不同的声腔,成为多声腔剧种。因此可以说,戏曲剧种是用来区分不同戏曲品类的整体概念,而戏曲声腔包括与腔调密切相关的文学构成、演唱方法、腔辞音调、乐器场面和组合手法等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的概念,成为区分不同戏曲品种的重要的元素材料。这也是洛地先生多次著文反对“以戏曲作为中国戏剧的统称”[12],并将“以曲腔史替代戏剧史”[13]视为中国传统戏剧研究的缺憾的真是内涵所在。 “婺剧”的命名正是在这样的戏曲文化背景中诞生的,因此我们说,“婺剧”的命名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目前,对“婺剧”概念的质疑主要是所指过于笼统,“不能恰当地表现它的内容和性质的。它只是在某一地区范围内,几个相当久远历史的剧种,所残存下来的剧目共同应用的名词。”[14]“婺剧,是浙江省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剧种,而是高腔、昆腔、乱弹、徽戏、滩簧、时调等六大剧种的总称。”[15]“婺剧”的“名字是雅了,却把浙江省的戏曲系统搞乱了。……笼统称为‘婺剧’就制造混乱了,给研究剧种的同志增加了许多麻烦。”[16]“‘婺剧’作为剧种名称,其词义同金华戏一样,总是被理解为‘流传在金华地区的各种戏曲’。……这是很难理清‘婺剧’一词词义的重要原因。”[17] 笔者以为,此种担心大可不必。一般说来,但凡剧种的命名都有从泛称到专指的演变过程,以“豫剧”为例,王培义于年12月15日-年3月16日在《京报副刊·戏剧周刊》上连载《豫剧通论》,从文章内容分析,这里所说的“豫剧”是河南戏剧的总称;至年晚清举人邹少和撰著的《豫剧考略》之“豫剧”指代依然如故;但今天的“豫剧”却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河南戏剧的总称”的理解。作为多声腔剧种而早于“婺剧”命名的“京剧”、“川剧”、“粤剧”、“湘剧”和略晚的“赣剧”(年)、“绍剧”(年)、“和剧”(年)、“瓯剧”(年),同样经历从泛称到专指的演变,如今概念所指已非常明确,为什么“婺剧”就不行呢?看来,还是我们的观念和认识尚需转变和更新。 值得强调的是,作为多声腔聚拢的“婺剧”,并没有将建国初期流行于金衢地区的所有声腔照单全收,而是有目的、有选择地将时年搬演于金衢及周边戏曲艺术舞台的、在国内名气更大、影响更广的京剧和越剧排除在外,这种对地方本土戏曲文化的钟爱与维护,同20世纪初川剧“高腔维持会”呼吁“挽救高腔”,在全川倡导“‘唱川剧就要唱高腔,唱胡琴不啻给京戏帮行’的宣言”[18]是何其的相似,虽说比“川剧”的命名迟约二十年,但其作为多声腔剧种概念的指代、剧种的本质及声腔间的内在关系却是一致的。大量的高、昆、乱“三合班”和昆、乱、徽“两合半班”频繁的舞台演剧实践;为便于受众的听辨,“高、昆、乱、徽、滩、时”等六声腔戏班统一使用金华官话;乐队场面(除主奏乐器外)、脚色行当、表演风格、服装、化妆(脸谱)、道具渐趋统一,甚至表演剧目亦有很多重叠,艺术表现手段及艺术审美特征一致性的增多,都自然而然地成为“高、昆、乱、徽、滩、时”六声腔聚合的重要前提,也是必然结果。声腔聚拢,合班不合腔,合而不混,和而不同。 而更令人深思和玩味的是原本演唱越剧的龙游人周越先、周越桂姐妹,却因越剧在金衢地区受众群体相对窄狭,而于年加入“周春聚戏班”改唱婺剧,以至于解放后成为著名的婺剧表演艺术家,并且有业内人以“周派”[19]名之,这就从更深层的文化人类学视角,凸显了婺剧作为婺文化组成部分的强烈排他性,证实了婺剧与婺州人的天然亲和性。 [1]谭伟、卢笑鸿:《婺剧》,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版,第页;谭伟:《婺剧》,载《中国戏曲志·浙江卷》,北京:中国ISBM中心年版,第99页。 [2]章寿松、洪波:《婺剧简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年版,第5页。 [3]傅谨:《婺剧:腔调与剧种》,《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年第1期,第27页。 [4]方宏烨:《试论婺剧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年第6期,第47页。 [5]徐珂编撰:《清稗类钞选(文学艺术戏剧音乐)》之“串客”条,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版,第页。 [6]王骥德:《方诸馆曲曲律》,载傅惜华编《古典戏曲声乐论著丛编》,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年版,第46页。 [7]余从:《高腔与川剧音乐·序》,载路应昆:《高腔与川剧音乐》,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年版,第2页。 [8]商丘宋时称归德府,笔者以“归德调”替代狭义上的“豫东调”唱腔流派,旨在廓清“豫东调”的广、狭意义,避免不必要的概念混淆。 [9]马彦祥、余从:《“戏曲声腔、剧种”概说》,载《梆子声腔剧种学术讨论会文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年版,第90页。 [10]洛地:《我国戏剧被称为‘戏曲’的征问》、《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中的缺憾一二三》,载胡忌主编《戏史辨》(第2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年版,第5页、第4~13页。 [11]武俊达:《戏曲音乐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年版,第页。 [12]洛地:《我国戏剧被称为‘戏曲’的征问》,载胡忌主编《戏史辨》(第2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年版,第5页。 [13]洛地:《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中的缺憾一二三》,载胡忌主编《戏史辨》(第2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年版,第13页。 [14]严敦易:《元明清戏曲论集·婺剧观感》, [15]章寿松、洪波:《婺剧简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页。 [16]戏曲理论家马彦祥给《婺剧简史》的作者章寿松、洪波的回信。 [17]金华市艺术研究所编:《中国婺剧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年版,第6页。 [18]戴德源主编:《成都市志·川剧志·川剧艺术》,成都方志出版社年版,第页。 [19]楼敦传:《婺剧流派唱腔艺术漫谈》,《金华日报》年1月5日。 (本文发表于《戏曲艺术》年第1期,为“’中国婺剧理论学术研讨会”而作。)赞赏 人赞赏 长按中科白癜风医院微博贵州最好的白癜风医院
|
当前位置: 松阳县 >以剧种视角解析婺剧命名的有效性
时间:2017-10-24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动态证照合一啦,对面的三小业主看过来
- 下一篇文章: 松阳当代国际艺术展到了云端觅境画风是酱紫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